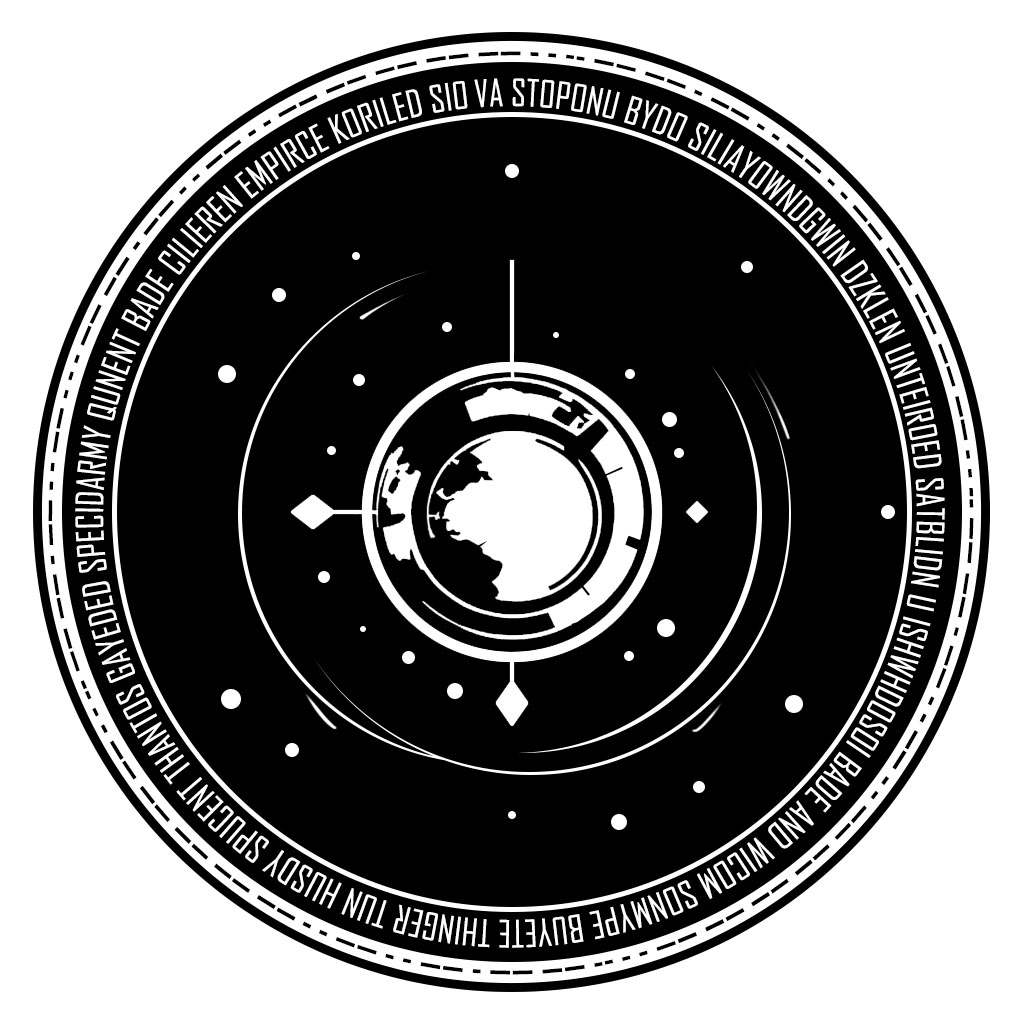拉尔普东部 仁安四年 大陆历一千三百八十七 凌冽月 水耀
齐老太爷眯缝着眼,盘算起自己的日子来,估摸着应该有个九十来年。头发白得跟冬天的雪似的,背驼得像是家门口的老槐树。
“爹,天凉了,回屋吧。”年轻人站在他身后,身形似乎并未比父亲健壮多少,一样的枯瘦,一样的佝偻。
齐老太爷没回头,只是伸出手指,指了指远处山腰上那排灰扑扑的小砖房:“德隆啊,我看着,那是养老阁吧?”
齐德隆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,没吱声。
“我寻思着,时候差不多了。”齐老太爷慢悠悠地说,声音沙哑得像风吹过干枯的芦苇:“你娘走那年,我才七十出头。如今我都九十了,活够本了。”
齐德隆的膝盖一软,差点跪下去:“爹…我能养你,咱家不缺粮,,,”
齐老太爷摇了摇头。这是村里的规矩,对岸的老太太脑袋灵光,牙齿还能咬开东杏果,不也被送了进去?他想着,不能让儿子在村里惹上白眼,更不能丢了体面。
养老阁,这名字听着体面,实际上是个活人坟。村里老人到了岁数,儿女们就得按规矩把老人送进去。先是一副薄棺,抬到山腰那排砖房里,然后一天添一块砖,直到把门封死。如果老人不愿进去,或是半路跑了出来,就得抓起来绑在火架上烧死,都说那不是本人了,只是山里的精怪占了身体。
说来也奇怪,曾被称作“精怪”、“怪物”的异族们离此处不远,那几场战争的伤痕却早已随着被“变成”精怪的老人们入了土。老人们被赶着进去,等洞口彻底封死,那矮房便成了坟。
第二天一早,村里的木匠刘三来了,后面跟着村长。刘三扛着几块木板,一进门就嚷嚷:“齐大哥,您放心,我给老太爷打的棺材,保准结实!”那架势像是有什么喜事。齐德隆没搭理他,他也不恼,摇着头到一旁叮叮咚咚起来。
何尝不是喜事呢?老人进了养老阁,是要把儿女的厄运都从阳间带走的。少一口人吃饭,收一笔礼金,儿女或是置办新房、或是娶夫生子,都是好的。
齐老太爷坐在堂屋里,穿着一身崭新的藏青色寿衣,看着刘三喜气洋洋地卖力做活。他摸了摸衣服的面料,眼神有些呆,真好啊,若不是要入土了,人总是穿不了这么好的衣服的。
晌午时分,村里有头有脸的老人陆续到了齐家院子。八十岁的赵太公拄着拐杖,颤巍巍地拍了拍齐老太爷的肩膀,一样眯着眼,什么都没说。倒是隔壁的王婶子笑开了花,嘴里巧着什么喜丧、什么消灾之类的话,瓜子皮遍地都是。
齐老太爷只是点头,多说不出一句,像是恐惧,像是麻木。
“吉时到了!”不知谁喊了一嗓子。
刘三与三个女人抬着那口刚打好的棺材进了院子。棺材没上漆,露出木头本来的浅黄色,散发着一股奇异的香味,闪着微微的荧光。按规矩,时候已过,老太爷已是死人了,须得子女抬进棺里。但齐德隆颤着手,几次使不上力,最后是村长吆喝着,众人把齐老太爷抬了进去。
人群抬着棺材往山上走,齐德隆捧着父亲的牌位走在最前面。牌位是新刻的,黑底金字,写着”显考齐公讳永福之灵位”,请了某处的道士开了光,说是能保三千年不朽不坏。齐德隆有些悲戚,道士能让排位千年不朽,却无法劝说这区区百年的规矩。
山路崎岖,棺材晃晃悠悠,齐老太爷躺在里面,透过棺材缝看着天,想起六十年前他抬着自己父亲上山时的情形。
养老阁是一排半地下的砖房,每间约莫五尺见方,有门无窗。棺材被抬进其中一间,轻轻放在地上。齐德隆跪在棺材前,磕了三个响头。
“爹,儿子不孝…”
第一块砖是赵太公亲手砌的。老人颤巍巍地抹上泥浆,把砖贴在门框边上。”老哥哥,你先走一步,我随后就到。”
众人散去后,齐德隆独自跪在养老阁前。夕阳西下,山风渐起,吹得他后背发凉。棺材里传来父亲的声音:”回去吧,明天记得带块好砖来。”
第二天一早,齐德隆就扛着一块青砖上了山。砖是他昨晚亲手烧的,掺了稻壳,烧出来格外结实。
“爹,我来了。”他站在门前,看着昨天砌的那块砖已经和泥浆牢牢粘在一起。
棺材里传来咳嗽声:”嗯,添砖吧。”
齐德隆抹上泥浆,小心翼翼地把第二块砖垒上去。透过砖缝,他看见父亲坐在棺材里,正在吃他昨天留下的馍馍。
“爹,您还缺啥不?”
“不缺啥。”齐老太爷啃着干馍,声音含糊,”就是夜里有点冷。明儿个给我捎床被子来。”
第三天,齐德隆不仅带了砖,还抱了一床棉被。砖墙已经有三层高,齐老太爷只能蜷缩在棺材里,从上方透进来的光线看书。
“爹,看久了伤眼睛。”齐德隆递进去一个油纸包,”这是您爱吃的驴打滚。”
齐老太爷接过点心,突然抓住儿子的手:”德隆啊,记不记得你七岁那年掉进冰窟窿里?”
“记得,是爹您跳下去把我捞上来的。”
“那水真冷啊…“老人松开手,喃喃道,”比这养老阁还冷。”
砖墙一天天增高。到第七天,已经齐腰高了。齐德隆每次来都要带点东西——一壶老酒,一包烟丝,甚至是一只蝈蝈笼子。父子俩隔着砖墙说话,多半是齐老太爷讲古,齐德隆听着。
第二十天,砖墙已经高过头顶,只留下一个一尺见方的洞口。齐德隆搬来梯子,趴在洞口往下看。棺材里的父亲瘦了一圈,白发蓬乱,但眼睛依然有神。
“德隆,去把我那件新棉袄拿来,我走的时候得穿暖些。”
第二十五天,洞口只剩下一个砖的空隙。齐德隆带来的是最后一块砖。他的手抖得厉害,泥浆抹得到处都是。
“爹…“他趴在最后的洞口,声音哽咽。
齐老太爷已经穿好了棉袄,头发梳得一丝不苟。他躺在棺材里,双手交叉放在胸前,像个准备入睡的孩子。
“来吧,把砖砌上。”老人平静着闭上眼。齐德隆把最后一块砖慢慢推向洞口。光线一点一点消失,最后只剩下一线光亮时,他听见父亲说:”等等。”
他赶紧把砖往回拉。齐老太爷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:”德隆啊,给我梳梳头,刚才可能没梳好。”
齐德隆哭着从洞口伸进手去,摸索着给父亲整理头发。那些白发稀疏干枯,像秋天的芦苇。
“好了。”齐老太爷说,”这回真好了。”
最后一块砖彻底封住了洞口。齐德隆跪在严丝合缝的砖墙前,听着里面隐约传来的咳嗽声渐渐微弱,直到完全消失。
山风呜咽,像是无数亡魂在哭泣。齐德隆的额头抵在冰冷的砖墙上,直到夕阳西下,直到繁星满天。
养老阁又多了一间住满的房子。